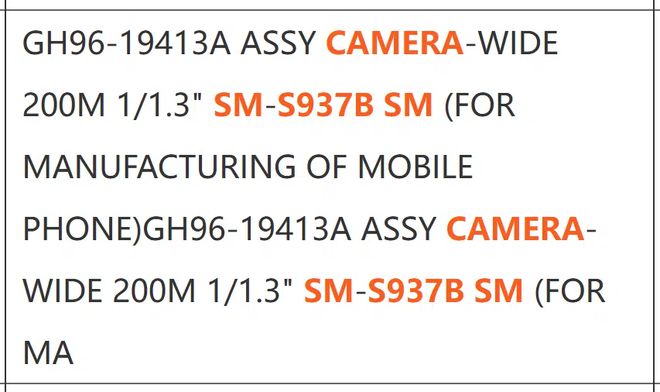本文将聚焦于教皇方济各的殡葬典礼,探讨各国政要的出席情况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国际关系、宗教因素等。涉及到普京不能出席的原因、中方送出十字背后的外交考量,以及新教皇选举背后的种种复杂因素等内容。
教皇方济各辞世后,梵蒂冈将于4月26日为其举行盛大的殡葬典礼。这一典礼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因为诸多国家的政要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各国政要们对待此次殡葬典礼的态度各有不同。特朗普宣称将和他的妻子亲自前往罗马出席葬礼,并且还下令美国所有使领馆降半旗哀悼,他公开赞誉方济各是“这个时代最有分量的声音之一”。这看似单纯的致敬行为,背后却暗藏玄机。毕竟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在移民、宗教政策方面存在诸多争议,他参加葬礼的举动,既是表达对教皇的敬重,同时也是在修复与天主教选民之间已经产生的裂痕。泽连斯基表示自己也会到场,马克龙同样不会缺席这场葬礼。然而,普京却无法前往。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普京本人不会出席葬礼,只会派出外交代表团。这一决定有着现实层面的考虑,当前普京出境面临被捕的风险,所以即便他内心对方济各充满敬重,也无法亲自前往。这一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在“宗教距离”上依然存在隔阂。中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克制。外交部只是表示中方表示哀悼,并且希望与梵蒂冈继续保持建设性接触。对于是否会有代表参加葬礼并没有给出确切答复,仅仅送了十个字:“推动中梵关系持续改善。”这一态度背后有着复杂的外交因素。中国和梵蒂冈至今尚未建交,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梵蒂冈仍然承认台湾;二是主教任命权问题尚未谈妥。虽然2018年双方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主教人选由中梵协商,但一直处于“试运行”状态,并且该协议后续续了三次,最近一次是在2024年。所以中方目前的态度既不能过于热情,也不能完全冷淡对待,很可能会参照2005年的做法,让驻意大利大使“顺路”参加葬礼。方济各在位的十一年间,在天主教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是第一位拉美教宗,也是第一位耶稣会出身的教皇。他与传统意义上“避世”的神职人员不同,更像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外交家,频繁针对地缘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有时甚至比世俗政客表达得更加直接。例如在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之时,全世界纷纷站队,他却说出了北约东扩也是问题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话。他既不偏袒乌克兰,也不袒护俄罗斯,而是一直强调“停止战争”“和平调解”,甚至主动提出愿意访问莫斯科会见普京,不过俄方始终没有同意。这其中存在宗教方面的因素,在俄国宗教领域一直是东正教占据主导地位,天主教想要涉足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普京在方济各去世后还是发了唁电,称他是“人文主义和正义的捍卫者”。除了殡葬典礼之外,新教皇的选举也备受关注。按照传统,葬礼之后的两到三周内,梵蒂冈将会召开秘密会议,由枢机主教团进行投票来选出新任教皇。选举制度并不复杂,只要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即可当选。但是谁能够最终获胜却难以预测。方济各在任期内提拔了超过80%的枢机,这些枢机很多都来自非洲、拉美、亚洲。他们背景多元,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欧洲派枢机有所不同。目前呼声较高的有三位候选人:意大利的帕罗林,他是老资格,对教廷外交十分熟悉;菲律宾的塔格莱,他是亚洲的代表,深受方济各的信任;加纳的图尔克森,他是非洲教会的代表人物。如果塔格莱或者图尔克森当选,那将意味着“南方教会”真正崛起。选举过程虽然不透明,但影响深远,因为新教皇是否会延续方济各的改革,是否会对中梵关系释放更多信号,都取决于这场闭门会议的结果。方济各在任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布局,试图推动“去欧洲中心化”。过去教皇大多来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他上台之后,大力提拔了数十位来自南美、非洲和亚洲的枢机主教。他多次强调“教会是全球的,不是西方的”。他的做法是将话语权下放,让南方国家在教会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一举措让教廷内部的选举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权力分散化”的背后是他对教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尝试。他希望打破过去教会层级森严、集中封闭的传统,让更多的教区、更多的声音能够参与到重大决策之中,例如在主教会议、地方会议上,他都尽可能地扩大参与范围,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安排,更是他神学理念的实践,他坚信教会不是某些精英的舞台,而是信众集体信仰的共同体。本文总结了教皇方济各殡葬典礼上各国政要的出席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包括普京因现实风险无法出席、特朗普出于大选考量出席、中方因外交关系现状而态度克制等。同时也阐述了新教皇选举背后复杂的因素,如不同候选人的情况以及选举结果对教会和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提及了方济各在位期间的改革举措及其意义。
原创文章,作者:Admin,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otfound404.org.cn/gcnews/2455.html